理性·建设性

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英国文学著名的“移民三杰”之一维迪亚达尔·苏雷基普拉萨德·奈保尔爵士于2018年8月11日去世,享年85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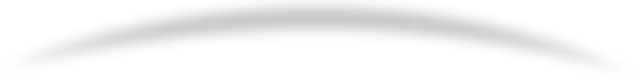


“世界本该停止,可它还在继续”
之所以选择用这样一个开头来纪念伟大的作家奈保尔,源自我阅读他的时候,感受到的他文字间那种凛然、强悍而又紧张的气质。奈保尔是那种自带犀利气场的思考型作家,读者面对他呈现的新鲜的生活、别样的历史讯息和密集的真知灼见时,会自然而然产生知识、阅历、智商和思考力上的自卑感,甘愿被他启发、被他“教训”,甘愿对他望尘莫及。
据说,生活中的他也是一个极易紧张和愤怒的人,除了抨击政客,对记者不买账、动辄和出版社闹翻、对情人大打出手之外,他在《看,这个世界》中对作家同行的褒贬,在《巴黎作家访谈录》中与采访者的对谈,都充满了火药味。他敏感、善辩、粗鲁、思维活跃、咄咄逼人,他时时想要展现自己思维的肌肉和智力的胸毛,让人发怵。他仿佛就是要用一股才华与世界碰撞过程中激发出来的愤怒的力量,征服世界、征服读者。
打开他的书,无论哪一本,即便是他最为中国作家们称道的、回忆童年生活的《米格尔街》,其间弥漫的忧伤和温情也是充满了紧张感的——一种叙事结构上的紧张感(这一点只需对比阅读赫拉巴尔同样描写童年的《甜甜的忧伤》就会立刻明了)。难怪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会这样形容他的写作:“将深具洞察力的叙述和不受世俗侵蚀的探索融为一体,迫使我们去发现被压抑的历史的真实存在。”这被“压抑的历史”就是“后殖民时代”的印度、非洲、加勒比海、拉美、亚洲等等,尤其是他的母国印度。与因文化乡愁而忧伤多情的作家不同,奈保尔的文化寻根越热切,对母国文化的质疑和批判就越无情和冷峻。
他说:印度的贫穷、种姓制度、被殖民的遗迹让人绝望,而印度人却沉迷在宗教之中,把残酷的世界看作一个“幻象”来自欺欺人;他们缺乏“种族感”,无法认清过去和未来的关系;一直在用悲情,甚至滥情的方式阐释历史,寄生在历史中,闭眼享受着“枷锁般的舒适”。消极、虚无的印度,所面临的危机是“一个衰败中的文明的危机,其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更迅速地衰败。”而印度人的盲目乐观,“就像长在粪堆上的玫瑰”,让人想起来就感到痛苦。(《幽暗国度》《印度:受伤的文明》)
真相残酷,而奈保尔从不打算回避。
直面残酷,一般都是领教过生活无情的强者的选择。奈保尔出身卑微,外祖父早年作为佣工从印度迁居到特立尼达。而他从外祖母的乡间宅邸,到黑人西班牙港,最后又到了伦敦,到了牛津大学,一路漂泊,一路困顿,也一路增长知识和认识自己的能力。最后他选择写作作为理想抱负,开始从坚硬的生存困顿中挤榨出文字,从一度都想自杀的绝望中挤榨出文学的鲜血。
他在半自传体小说《半生》中写,离开家乡到伦敦的威利,一筹莫展,痛苦万分中他领悟到:一切都偏离了正轨,世界应该停止,可它还在继续。而他反复被引用的,《大河湾》的开头,更是在说这种痛苦的领悟:“世界如其所是。那些无足轻重的人,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,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。”
奈保尔大概属于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的人,属于见识了现实的残酷依然正面强攻的人。他说:生活在黑暗角落里的人也有自己的灵魂,而他用写作给这卑微的灵魂找到了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,独一无二,光彩熠熠。
他笔耕不辍50多年,为世界文坛留下了30多本著作,中文译本至少有27种之多,包括小说、游记纪实、回忆录、随笔,而且几乎每一本都不会让人产生阅读的熟悉感和厌倦感。其中以父亲为原型的小说《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》被列入兰登书屋、现代图书馆20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;以非洲为主题的《大河湾》,被《》《卫报》《每日邮报》等列入世纪百部经典。而享誉世界的“印度三部曲”《幽暗国度》《印度:受伤的文明》《印度:百万叛乱的今天》更是无可替代。因为写作上的巨大成就,他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,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;也因为写作上的无可替代,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受到了全世界的悼念。
《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》:像男人一样可怜父亲
几乎奈保尔所有的小说,都有他自己或者他父亲的影子。这是他有意识的追求。他想通过跟自己有着相同背景的角色,缩短虚构和真实之间的距离。而在世界级的大作家中,很少有作家像奈保尔一样,从男人对男人的角度,崇拜和理解父亲。他说,对自己创作影响最大的是父亲写的、从未出版过的故事,而自己之所以将写作当作抱负,也是要遵循父亲的榜样,是父亲的笔让他初识世界残酷,也让他发现内省的重要。
他把创作启蒙归因于父亲,归因于自己的血缘和文化之“根”,自然也会用重要的创作献上对父亲的感念和体恤。在《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》中,他用50万字的篇幅写“父亲”和房子的关系,写父亲穷困潦倒而无从改变的一生。在半自传体小说《半生》和《魔种》中,他始终不忘父亲,尤其是在检省自己对“性”观念的认识,对贫穷、沉默、忧郁的理解,对生命意义和死亡的认识的时候,他也总是对比父亲与自己,两个身处不同时代、不同空间中的男人的不同。
从某种角度说,奈保尔一生都在写父亲,写自己,写自己文化上的无家可归。他说:“一个作家的半生工作,就是发现他的主题。而我的问题在于我的一生有太多变迁,充满了动荡和迁徙”,“我这辈子一直在做这么一件事:在哪儿都找不到家,只是看起来像在家里而已”。在这样的过程中,他不知道要“把目光投向何处”,于是,他开始四处寻找,最终,他选择了父亲和自己。
毕司沃斯先生,从懂事开始就想生活在“一个可以实现雄心的国度,并且那些雄心壮志总有意义可言”。然而,无从改变的贫穷,无从改变的生存空间——小小的特立尼达,种姓制度下入赘的婚姻,大家庭中相互抱怨、相互消耗的琐碎,终于让父亲慢慢向生活投降。为了拥有自己的房子,为了实现一个男人的“独立自主”,父亲在求职、失业、再求职的路上反反复复、兢兢业业、本本分分、克制忍耐。他推迟了所有的快乐,然而,世界却从未因此给他半点甜蜜和快乐。他始终没有自己的房子,没有自我得以保存的空间,没有男人的尊严,没有未来。
如果整部小说只是写父亲如同中国的《骆驼祥子》般被时代和生活碾压的悲剧,控诉社会,或许力量感会弱一些。不同的是,奈保尔写了一个善于自我修复和自我鼓励的父亲,他拥有令人过目难忘的、深刻的内心生活。甚至为了描述他内心的曲折,奈保尔不惜让小说显得冗长。白天残酷的现实把父亲撕扯得越支离破碎,夜晚他的自我修复越显得忧伤动人。
在访谈中,奈保尔曾说,他深深地知道,身处特立尼达的父亲,早早被婚姻和孩子、被大家庭束缚住的父亲,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自己悲剧性的一生,而自己,之所以能够避免父亲的命运,只是因为逃离了特立尼达,来到了更广阔的世界。这广阔或许会带给人渺小感和无力感的伤害,但它也给了人实现自我的无限的可能;使人在这世上软弱无能的东西,也能让人同时变得有价值。
在文学中,把人的处境、命运与世界的变化、立场的转化,如此辩证真实、如此不悲情、不幽怨地联系在一起,是奈保尔作为世界级大作家的宏阔伟大之处。
小说中几处细节让人印象深刻:一是母亲对父亲的称呼总是“男人”,对一个入赘的、经常失业、要靠丈母娘救济的人来说,这听上去更像是讽刺。二是父亲找到记者的工作之后,为了报纸的发行量而编写耸人听闻的假新闻,他写的每一条都跟自己的孩子、家庭和房子有关,都是真实的,他把一个父亲的惦念和一个男人的梦想写进了所谓的“假造新闻”中,其中一篇的标题甚至都是《父亲在棺材中回家》。三是父亲为了搬出大家庭,终于鼓起勇气要向姨父家借钱。他总想开口,但总是被打断,最终他悻悻而归,又一次被现实和自己的尊严打败。这时候小说写道:“毕司沃斯先生摇摇晃晃地坐在灯光幽暗的公车的木头座椅上,经过寂静的田野,经过那些没有灯的死寂的房子或者明亮的安静的房子,他现在不再去想他下午的使命了,他想的是他要面对的黑夜。”
黑夜无尽,房子遥遥无期。但男人可以悲伤吗?可以怨天尤人吗?只能再去寻找、再去奋斗。最终,父亲因为做了记者,得以借高利贷买了房子,但债还没还完,他就病了,在四十六岁的年纪抛别人世。有意思的是,中国的出版商把这本书定位为“百分之百的房奴之书”。
可以说,男人的“贫穷”和“漂泊”是奈保尔写父亲和写自己的关键词,而寻找立足之地,寻找安身之所,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,则是硬币的另一面。在这个过程中,奈保尔找得很辛苦、很勤奋,但他靠着从父亲的教训中得来的对世界“深刻的轻蔑态度”,获得了“充分的自觉和长久的孤独”,同时,也获得了“所向无敌的力量”。
奈保尔说,人的一生中,不知道要走过多远的路,才能找到自己想要面对的自己。为此,他冲破自己的生活环境、教育环境、文化束缚,践踏过去、冲破自己的写作领域,不断旅行以获得素材和灵感。他几次回到印度,深入非洲,重返加勒比。他不断思考和探索,努力让自己的内心配得上世界的宏阔,努力让自己的文字配得上自己踏过的生活荆棘和承受的思考之苦。
如今看来,《半生》中,外省编辑给自己写的讣告或许也可以看作奈保尔写给自己和父亲的——事实上,两个人在他的作品中早已水乳交融——“他最深刻的生活在他的心灵之中。但新闻工作的本质就是转瞬即逝,他没有留下任何纪念。爱情,那神圣的幻象,从没有触碰过他。不过他与英语痴缠终生。”
奈保尔本人当然有情感生活,也有两次婚姻,但在感情上,他的善变、粗暴和无情也是文坛八卦之一。他的作品中,的确没有动人的爱情描写,甚至,连可爱的女性角色都没有,而且,因为他粗暴的性描写和性想象,他还广被诟病。
从角色而言,他只是完美地完成了自己。
《大河湾》:谁的非洲?
也许,在奈保尔刻画过的女性形象中,《大河湾》中历史学家雷蒙德的妻子耶苇特算是一个例外。她年轻貌美,直率坦荡,她跟随被总统赏识的丈夫来到非洲,住在总统建设的“领地”里,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,然而,她先后和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因达尔、跟非洲小镇的杂货店主“我”保持着情人关系。她显然不属于非洲,她恐惧非洲,但她是年长丈夫的附属品,之后也很快沦为情人的附属品——在非洲,即使是来自欧洲的、受过教育的女性也会沦落到被打耳光的境地。
在一部短短20多万字的《大河湾》中,奈保尔以一个杂货店主的视角,通过写他和家奴、被资助人、非洲当地人、小镇上的其他店主等的交往,把非洲独立运动的困境,奴隶制度和种族制度的困境,宗教问题的困境,非洲与欧洲和阿拉伯的关系,非洲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,新非洲人和非洲新人的种种可能,全部囊括进来,体现了非凡的文学创造力。
他写非洲人多年来对秩序和金钱的向往;写他们因被殖民、被剥夺、被歧视而产生的深沉的愤怒;写置身非洲大陆的文明废墟中最容易产生的时间感和历史感的错乱;写战争、贫穷给非洲留下的脆弱的信仰;写这里的人们,无论来自何方,秉持何种信仰,内心的不安全感和无根意识;写这里没有公理,只有建立在权力、军队和腐败基础上的丛林法则;写新非洲人蔑视历史、认不清现实,自视甚高又残存着温和和软弱的心理;写来非洲淘金的文明人和白人,慢慢产生的依赖感、虚无感和难以改变的实用主义、物质主义、投机主义的立场。
奈保尔曾于1966年前往东非,在坦桑尼亚、肯尼亚和乌干达停留了八九个月,写下了《自由国度》(出版于1971年)和《大河湾》(出版于1979年)两部巨著。他用自己的观察和思索,深刻呈现移民一代找不到“家”的漂泊状态——非洲固然不安全,然而,逃离非洲之后却令人更加不适。于是书中那个几乎无所不能的纳扎努丁,只有不断地在全球飞来飞去,而“我”则在短暂的逃离后又选择回到了非洲——同时,也精准地直面了至今仍不过时的“非洲难题”。这是一个描写了“两个世界”——非洲和非洲以外的世界的作品,也是一个事关全球历史的作品,倘若作家心中没有宏阔的历史和文化的吞吐量,没有超越浅薄历史观和文化定见的判断力,根本难以想象。所以,《大河湾》才会被誉为奈保尔的巅峰代表作,也被《》誉为“最后一部现代主义的伟大史诗”。
小说中最为动人的情节是关于神父的死。这全书中唯一一个全心全意热爱非洲,并对非洲的未来充满信念的人,却死于非命。他的死,让“我”感觉,“整个世界也死了一小块”。接着,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:

标签: